跨市博弈丨AI熱潮下的GDP假象:泡沫何時破?
人工智能是21世紀最重要的科技革命,抑或只是一場顯而易見的經濟泡沫?答案很可能是兩者皆是。如同19世紀的鐵路和20世紀的寬頻網路,AI的劇本早已寫好:先是狂熱崛起,繼而猛烈崩盤,最終才真正改變世界。此刻,我們正處於第一幕的高潮,而劇院裏的每個人似乎都選擇性地忽略了舞台上搖搖欲墜的布景。
數字本身就在尖叫着「荒謬」。科技巨頭們今年預計將在AI基礎設施上豪擲4000億美元,這個數字已經超越了人類歷史上任何單一產業的資本支出。經通脹調整後,美國整個阿波羅登月計劃的總花費也不過3000億美元。這意味着,AI產業要求企業界每十個月就集體資助一次新的「登月計劃」。
更令人不安的是支出與回報之間的巨大鴻溝。到2026年,僅美國的AI資本支出預計就將超過5000億美元,約等於一個新加坡的全年GDP。然而,根據《華爾街日報》的報道,美國消費者每年在AI服務上的花費僅為120億美元——這大致是索馬里的GDP。如果你能理解新加坡與索馬里在經濟體量上的天壤之別,你就能領會AI領域中願景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裂谷。有些報告甚至指出,在那些仍在苦苦思索如何利用大型語言模型節省成本的大公司裏,AI的使用率實則正在下滑。
每個泡沫都有其回望時顯得格外刺眼的預兆。如今的凶兆比比皆是。一家名為Thinking Machines的新創公司,在尚未發布任何產品、甚至拒絕向投資者透露其業務方向的情況下,僅憑一句「我們正在與最頂尖的人才做AI」的空洞承諾,便籌集了史上最大規模的20億美元種子輪融資,估值高達100億美元。與此同時,股市早已脫離基本面,被一股純粹的動能所驅動。散戶們湧入AI概念股,並非基於對其盈利能力的分析,而是出於一種簡單的信念:其他人也正在湧入。
歷史上的每一次泡沫晚期,都伴隨着金融過度工程化的魅影。2008年金融海嘯前的擔保債務憑證(CDO)便是明證。不祥的是,AI似乎也正步入其自身的金融煉金術階段。正如《經濟學人》所指,AI的「Hyperscalers」——那些在AI上花費最多的科技巨頭——正巧妙地運用會計技巧來壓低其報告中的基礎設施支出,從而美化利潤。他們也開始將巨額AI支出轉移至資產負債表外的「特殊目的載體」(SPV),以掩蓋這場豪賭的真實成本。當企業開始費盡心機隱藏支出時,這本身就是一個訊號:泡沫已顯疲態,市場的耐心正在被透支。
這種瘋狂的資本支出正在對宏觀經濟產生扭曲效應。根據測算,2024年上半年美國GDP增長中,高達一半可能來自與數據中心相關的支出。這是一個令人咋舌的比例,意味着美國經濟的增長正被一個極其狹窄且高度集中的領域所支撐。這不是健康的有機增長,而是一場由資本強行灌注的虛假繁榮,其後果更是深遠的。
正如1990年代的電訊狂熱,AI正成為一個巨大的「資本黑洞」,將資金從經濟的其他領域無情地吸走。當年,電訊業的崛起推高了製造業的融資成本,最終加速了美國製造業外流。如今,歷史正在重演。當私募股權巨頭們發現,向數據中心開出數十億美元的支票,遠比向數百家小型製造商提供幾百萬美元的貸款來得輕鬆省事時,那些本應受益於製造業回流政策的實體經濟部分,便在無形中被釜底抽薪。資本的逐利本性與管理便利性,正以一種更陰險的方式扼殺着經濟的多元化。
這場盛宴的核心,還存在一個根本性的資產錯配問題。一個數據中心的成本結構極其扭曲:約60%的成本是壽命極短的GPU晶片,而壽命較長的建築物本身只佔一小部分。科技公司想把建築物當成長期資產攤銷,但其最有價值的部分卻在三五年內就迅速過時。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商業模式悖論,迫使企業在會計處理上玩弄各種「財技遊戲」,進一步加劇了財務的不透明性。
當本地居民開始反抗那些噪音巨大、耗電驚人的資料中心時(NIMBY,鄰避效應),將數據中心離岸外包至中東或印度等地,似乎是必然的下一步。這將使整個AI供應鏈變得更加脆弱和不透明。
最終,這場泡沫的破裂可能並非源於技術的證偽。鐵路和互聯網絡的泡沫破滅後,其技術價值依然存在。AI同樣如此。真正的引爆點,將是當投資者、信貸評級機構和監管者最終對這種「新加坡級支出、索馬里級收入」的模式失去信心,並開始審視那些被巧妙隱藏在SPV和會計附註中的真實債務時。屆時,我們需要關注的,將不再是下一個橫空出世的AI模型,而是科技巨頭們資產負債表上那搖搖欲墜的積木塔。整個金融體系都懸於Nvidia等少數晶片製造商之上,一旦這個支點鬆動,其連鎖反應將波及遠超科技行業的範疇。歷史不會簡單重複,但總會驚人地押韻。
徐立言(本欄每逢周一刊出)
www.facebook.com/hsulylab/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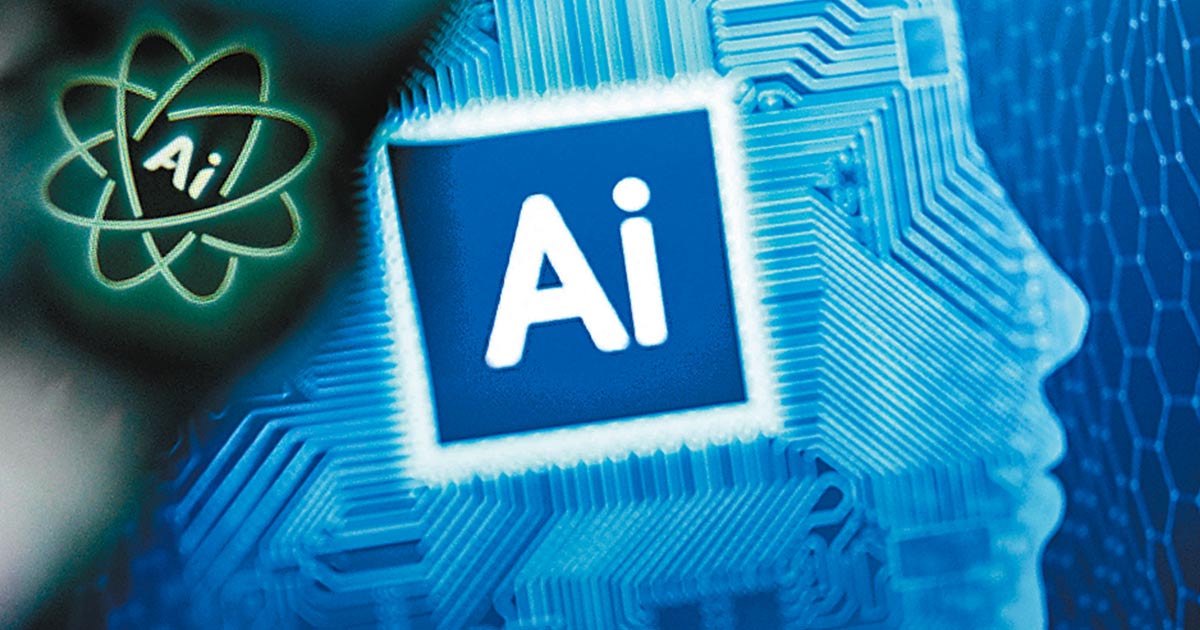




 ,泓滙財經資訊有限公司及財經智珠網有限公司提供。外滙及黃金報價由路透社提供。
,泓滙財經資訊有限公司及財經智珠網有限公司提供。外滙及黃金報價由路透社提供。